两类基金的“本质”并不在资产,而在决策与组织方式
主动基金与量化基金通常都以证券为主要投资对象,底层可以买股票、债券、可转债、期货或衍生品,也都可能以公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的法律载体存在。因此,它们的结构性差异不在“买的是什么资产”,而在“如何形成持仓、如何约束决策、如何把决策落到交易与风控上”。这点类似于讨论“商品期货与股票的结构差异是什么?标的属性根本不同”时强调的:关键在标的与机制;而在这里,关键在决策机制与治理结构。
主动基金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基金经理与研究体系:通过基本面研究、行业比较、公司治理判断、估值与景气度框架等形成主观判断,再转化为组合。量化基金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模型与数据管线:将可观测信息编码为因子、信号或规则,经过统计检验与约束优化形成组合,并通过程序化交易执行。两者都可能存在“主观环节”,但主观的位置不同:主动基金的主观多在“观点—组合”的前端,量化基金的主观更多体现在“变量选择、样本定义、约束设定、回测口径、执行假设”等结构化环节。
决策链条与制度约束:从研究到交易的“可复制性”不同
从组织结构看,主动基金常见的链条是研究员覆盖—行业/策略讨论—基金经理拍板—交易执行—风控与合规复核。其制度约束主要体现在投资范围、集中度、流动性、杠杆与衍生品使用、信息隔离与合规披露等方面;但在这些边界内,组合的形成依赖人的判断与会议机制,决策的可解释性往往以“投资逻辑叙述”呈现。
量化基金的链条更像工程流水线:数据获取与清洗—特征构造—模型训练/参数估计—组合构建(优化器/风险模型/约束)—交易算法执行—实时监控与回归测试。制度约束同样存在,但它们通常被“写进模型约束与风控阈值”,以参数化方式嵌入流程。由此带来一个结构差异:主动基金的流程更依赖“人治的稳定性”,量化基金更依赖“系统的稳定性”。当团队更替时,主动基金的投资风格可能随核心人员变化而漂移;量化基金也会受人员影响,但漂移往往表现为模型版本、数据口径、约束体系的变更,具有更强的可审计性与可回滚性。
在信息使用上,主动基金更偏向低频、非结构化信息:管理层沟通、产业链调研、政策解读、竞争格局变化等;量化基金更偏向高频、结构化信息:价格与成交、财务因子、文本与另类数据的结构化结果等。两者并非互斥,但“信息形态”决定了验证方式:主动基金常用案例推理与情景分析,量化基金依赖统计显著性、稳健性检验与样本外表现。
风险来源与回报形成:主动偏“判断误差”,量化偏“模型与交易误差”
主动基金的主要风险更接近“判断型风险”:对公司基本面、行业周期、估值中枢、政策约束的判断错误,或对市场情绪与流动性拐点把握不当。其回报更多来自对未来现金流与风险溢价变化的前瞻判断,表现为行业/主题暴露、个股选择与持有期收益。
量化基金的风险更接近“模型型风险”,常见包括:
1)数据与口径风险:幸存者偏差、复权处理、财务数据滞后、公告日期对齐、停牌与涨跌停处理等;
2)过拟合与结构断裂:历史有效的因子在制度、参与者结构或宏观环境变化后失效;
3)拥挤交易与相关性上升:同类模型集中在相似信号上,导致在压力情境下同时撤退;
4)执行与微观结构风险:冲击成本、滑点、撮合规则、交易限制、融券与保证金约束等,使理论收益在落地时被侵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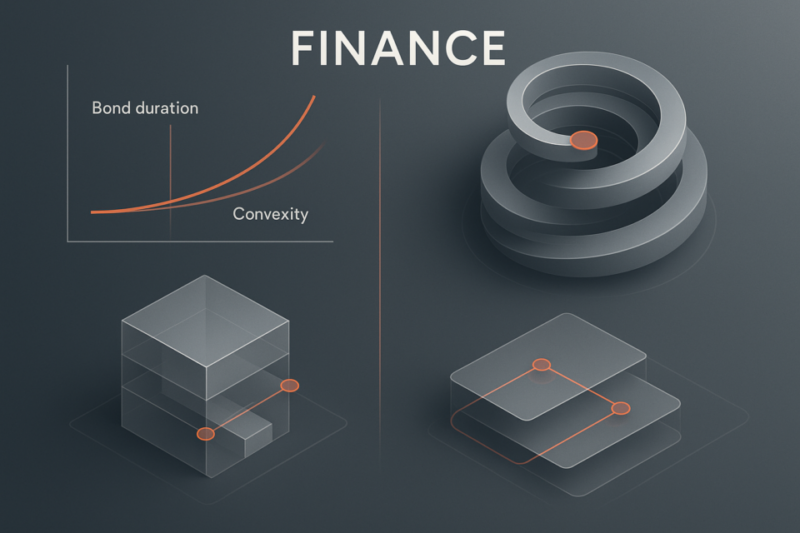
两者在“现金流”维度也呈现差异。基金本身对投资者的现金流主要来自申赎与分红安排,但底层资产的现金流解释路径不同:主动基金常以企业盈利、分红与估值修复叙事来解释组合现金流的可持续性;量化基金则更常以因子溢价、风险补偿与交易结构(如价差、期限结构、统计套利关系)来解释收益来源。即使底层同为股票,主动更强调“企业现金流—估值—价格”,量化更强调“可观测特征—风险暴露—收益分解”。
差异的底层原因:市场机制、参与者结构与可编码性
主动与量化的结构差异,根源在于资本市场信息的两类形态与两套处理机制:一类是难以完全量化的知识、经验与叙事,另一类是可被编码、可回测、可自动化执行的信号。哪些信息能被稳定编码,取决于制度环境(披露规则、交易限制、做空机制、杠杆与衍生品可用性)、市场微观结构(撮合方式、涨跌停、停牌、流动性分布)、以及参与者结构(机构占比、同质化程度、资金期限)。当这些条件变化时,两类基金受到的冲击路径也不同:主动基金更多通过“观点更新与仓位再平衡”响应,量化基金更多通过“模型再训练、参数重估、约束调整与执行策略更新”响应。
从治理角度看,主动基金的关键是投研权力如何集中与制衡:研究与交易、基金经理与风控、激励与合规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。量化基金的关键是技术与风险的共同治理:数据权限、代码审计、版本管理、回测与实盘隔离、异常交易与模型失效的处置流程。两者都需要合规与风险管理,但“风险被看见”的方式不同:主动基金更多通过持仓与逻辑披露被外部理解,量化基金更多通过风险暴露、因子归因、回撤分解与执行指标被内部管理。
因此,主动基金与量化基金的结构差异可以概括为:前者以人的判断与研究体系为核心生产力,后者以可编码的模型、数据与执行系统为核心生产力;前者的主要不确定性在认知与判断,后者的主要不确定性在模型有效性与交易落地。两者都在同一金融制度框架下运作,但在决策链条、风险来源、收益解释与组织治理上呈现出不同的“结构性”。




